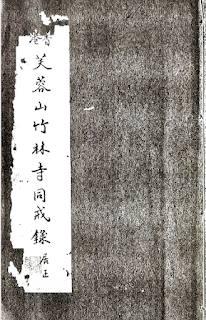香港幾乎所有的廟宇屬慈善性質,但香港並沒有監管慈善團體的法例,所謂的慈善團體或組織,其實只是按《稅務條例》第88條獲得慈善免稅的地位;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委”)在2013年12月6日發表了《 慈善組織》 報告書 (“報告書”)。
“香港目前沒有一套正式和既定的慈善組織註冊制度,亦沒有一個特定政府機構在這方面肩負整體責任。現有的慈善組織名單,例如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第88條獲准豁免繳稅的慈善組織名單,並不是一份包含香港所有慈善組織的全面和確證的名單,而慈善組織也並非必須把名稱記錄在這份名單內。由於沒有一份全面和確證的慈善組織名單,因此公眾人士無法在所有個案中確定某一組織的慈善組織地位。這個情況令人日益關注,因為這類組織為數不少,而且所籌募的金錢數額十分龐大。在公眾普遍支持下,法改會建議所有(一)向公眾募集現金捐款或其等值物的;及/或(二)已尋求豁免繳稅的慈善組織,均必須註冊。” - (報告書摘錄)
慈善組織的架構類別分別有據《公司條例》成立為法團的公司、社團及信託等;當中的社團組織,分為法團組織(根據《社團條例》註冊)及非屬法團組織(非法人組織),「曼華堂」便屬於一個非法人組織或準法人組織(quasi-unincorporated entity)不具法律地位,故此不能以組織的名義或代組織訂立合約、起訴與被起訴 (報告書3.4)。
 |
| 1963年擬定的章程 |
另一方面,以公司或社團架構運作的慈善組織,每年要公開其財務報表,公眾亦可通過查冊知悉相關組織的管理人是誰,達到一定程度上的監察功能;然而,「堂」因是 “傳統習俗組織”,沒有法律可以規管,同作為慈善組織,「堂」無需公開財務情況予公眾,「堂」成員更迭亦無註冊方式,一切由「堂」“說了算”。
法庭在一樁判決顯示了「堂」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下是如何的混亂:2017年10月30日,「曼華堂」在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議,任命三男士為管理層成員,所任命的三男士不是出家人,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是任何創始成員、堂的成員或前成員的徒弟,三人與堂沒有聯繫,只稱其為香港知名人士 ([2023] HKCFI 1392, 279) 。法庭認為,委任三名男士的決議,確實試圖違反《曼華堂簡章》,接納或任命這三位男士成為堂成員,這是一個令人嚴重關切的問題,因為現任成員似乎認為他們可以無視《曼華堂簡章》的規定,任命他們希望成為堂成員的任何人 ([2023] HKCFI 1392, 280) 。這些“任何人”一旦被任命,就可輕易掌控廟宇所有的一切,包括土地、管理和財產。
如組織內禁若寒蟬,誰人可有效監管?肯定的答案是近乎渺茫,因沒有「身份」去要求有關當局干預,也難以向法庭尋求濟助;2018年,上訴法庭就此問題作出了詳細分析;該上訴案的上訴人,正是向法庭要求頒令律政司司長以「慈善事業守護人」(paren patriae) 身分介入曼華堂(竹林禪院),作出更佳管理的安排,但在原訟法庭,被判定沒有「訴訟身份」(locus standi) 向法庭提出申索。
上訴庭直接推翻了原訟法庭的判決,指上訴人實際上超過或不同於普通公眾所擁有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可使他有資格提起訴訟 (針對曼華堂(竹林禪院)的混亂管理) (…materially greater than or different from that possessed by ordinary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ich may qualify him to bring this proceeding) ([2018] HKCA 488, 54)。
上訴庭歸納出三項理由:
- 香港對慈善團體的監管和和團體本身對公眾的責任;
- 佛教組織的架構;
- 構解法例第57A章(信託條例)時必須考慮香港和英國的差異
1. 慈善團體的監管和和團體本身對公眾的責任
香港公眾對慈善團體的監管和和團體本身對公眾的責任,遠遠落後於擁有完善和理想制度的英國,雖然在普通法下早已存在律政司司長以慈善事業守護人角式保護公眾利益,但以公眾對慈善團體的監管和和團體本身對公眾的責任而言,此並非適當的做法,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13年已就這些問題提出相當詳細的意見和建議,可惜至今還未進行 ( [2018] HKCA 488, 20, 33)。
2. 佛教組織的架構
南懷瑾(1918-2012),這個時代的一位重要禪宗學者,在他的著作《中國佛教發展史略》中指出,中國佛教在唐代的高峰期間,有十個不同宗派, 而每宗派各有其支派。到清朝末期,基本上只剩下三個主要宗派(基於中國佛教傳統),即「禪宗」, 「淨土宗」和「天台宗」。雖然民國時期對佛教的興趣有所恢復,今天情況仍然非常相似。但不像西方宗教,如天主教或英國聖公會信仰,在架構中有頂層的領導者,這些中國佛教宗派並沒有這樣的中央領導者。
儘管這種分散的形式,佛教的共同主旨(最簡單的形式),佛教徒遵循所有生物的平等和惻隱之心。他們還必須遵守行為和思想的規條。對於那些立誓受誡成為僧侶的比丘和比丘尼們,必須遵守更多與其身份相符的規條。「叢林制度」的規則也規範了佛教寺廟的運作和管理。申請人是否有資格啟動訴訟程序,需要重新考慮,以確保有關當局能夠妥善調查投訴。( [2018] HKCA 488, 52-55)
3. 香港和英國的差異
我們的法律體系有或異於外地,其次,我們的社會現實情況亦不同,這些差異會引出法庭在解構立法目的不同的結論。香港和英國的不同之處,香港佛教廟宇的情況在英國是沒有的,這種差異是在構解法例第57A章(信託條例)時必須考慮的,就本案眾多事實而言,上述提及的差異是引領我們給與上訴人身分一個更寬廣的構定。( [2018] HKCA 488, 57-58)
在該上訴案,林文瀚法官在慈善團體的監管和和團體本身對公眾的責任之部份作出極為詳盡的分析,但在法改委發表了報告書後的11年,仍沒有什麼進展和改變,可能是基於自身利益,也可能濫用宗教自由之名,總之,有關曼華堂(竹林禪院)的各項法庭裁決,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佛教廟宇。
BBF
延伸閱讀 - 2023年法庭判決